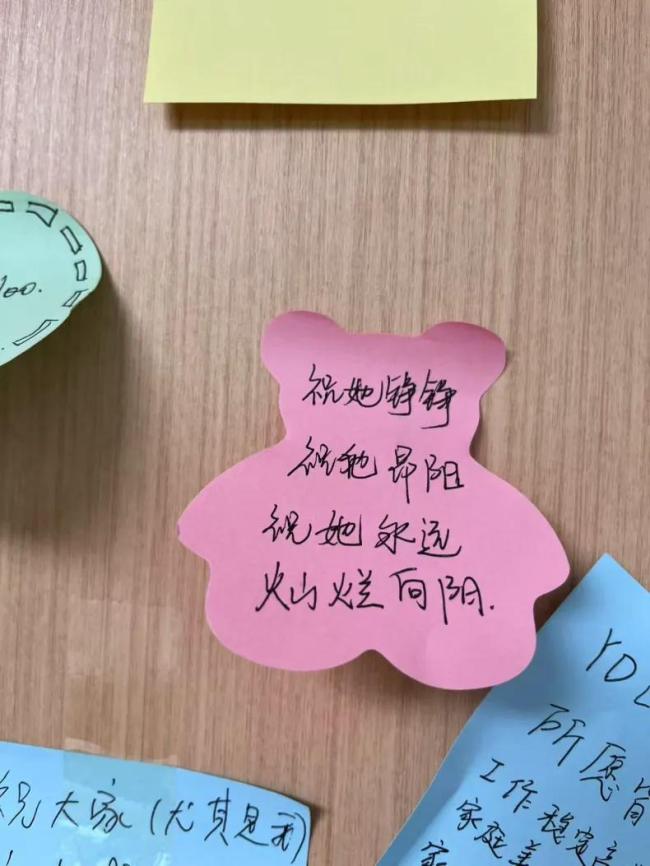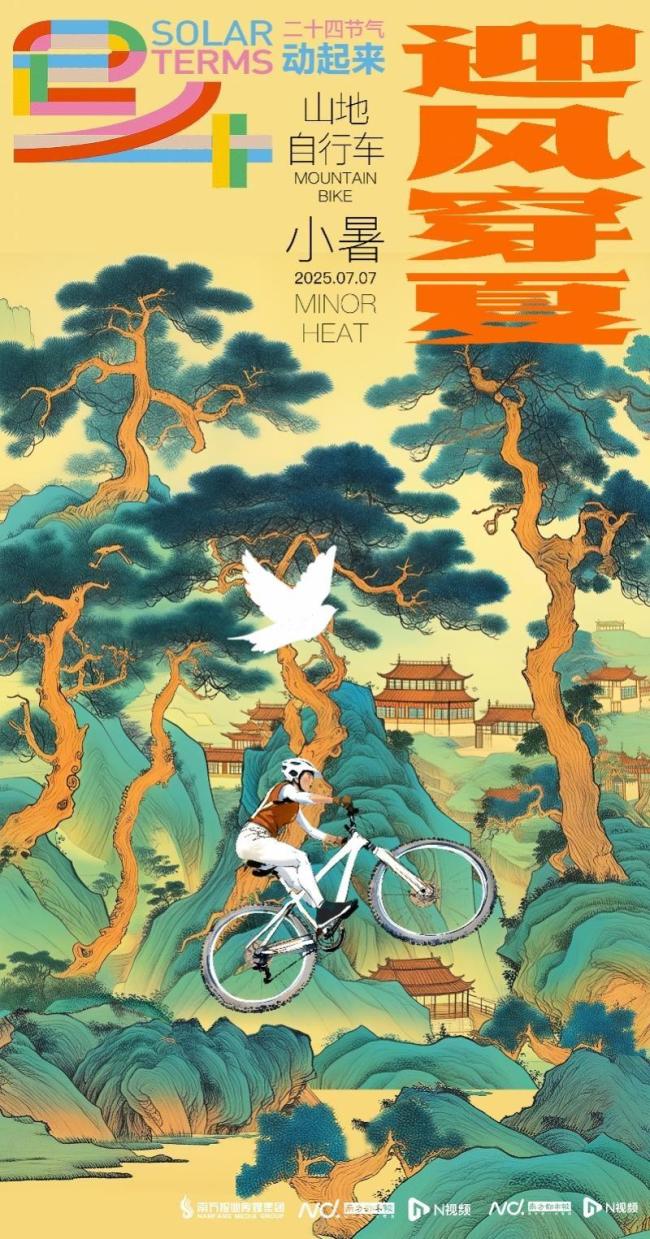研究生“退学潮”:他们为什么放弃?
近年来,研究生“退学潮”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学生选择放弃学业,原因多样,其中包括学术压力、就业前景、个人兴趣和价值观不符等因素,一些学生可能面临经济困难或心理健康问题,本文探讨了研究生退学现象背后的原因,关注学生们的真实需求和困境。
当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名校研究生退学,听起来就像是一次掉队。
据统计,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388万人,计划招生总人数为87.22万人,这意味着有将近300万人落榜。而在中国高校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博)中,每年约有50万人退学,在校生主动退学率接近3%。在研究生群体中,未按期毕业者占比高达四分之一。
近年来,尽管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进入研究生体系的门槛相对降低,但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心理压力并未随之减轻。相反,在学术要求、就业焦虑与个体期待的多重夹击下,不少顶着名校光环的研究生陷入持续的内耗与倦怠之中。
他们曾是被家人和老师寄予厚望的“尖子生”,如今却在课题中止、实验半途、论文未完的情况下选择离开。他们为什么选择放弃?我们找到几位退学的研究生,想要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与思考。
他们说,退学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积攒许久的委屈、恐慌与压抑突然找到出口。他们试图自救:有人去滑轮、画画、当主播、做电商、讲脱口秀,还有人搬去大理,在风大的海边告诉妈妈:“开滴滴也很开心”。
这意味着,他们愿意承认——曾经坚定选择的道路,如今已不再适合自己,于某个岔路口停下脚步,坦然面对内心的声音:也许这一切,不值得我继续下去。
退学那天,“我像个老鼠一样逃出实验室”
找导师签退学单那天,席萱尽量把自己缩进实验室的角落,生怕撞上任何人的目光。她低着头,文件夹捏在手里,汗出了一层。
“像只老鼠一样,”她回忆,“我干的是一件这么大逆不道的事。”
导师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她不敢直接敲门,只在门口踟蹰。这位导师是出了名的脾气大,一言不合就拍桌子骂人。大家背后称他是“院里的牌面”,一边调侃,一边敬而远之。
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她把退学表夹在文件夹里,站在办公桌前,把文件小心地推了过去。
“老师,我准备……我想退学了,请您帮我填一下这个表。”她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稳,不要颤抖。空气凝固了一瞬。导师抬头看她,只问了一句:“怎么想退学了呢?”
席萱舌头有些打结,机械地照着准备好的内容往下讲。她说自己做实验提不起劲,拖延严重,连心理咨询都试过了,还是无解。她努力维持语速平稳,甚至说到读书是父亲的期待,自己其实从没真正喜欢这个方向。话说到这里,她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全程,她只说自己哪里不行,绝口不提导师和实验室的半句不是。她不能激怒他。一次机会,不能出错。
最后,导师签了字。席萱夹起那张表,从门口走出去,像刚从密闭的深水中浮出水面,喘了一大口气。
退学,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对很多人来说,那张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背后,是年复一年的努力与代价。能走到这一步,本身就是一道筛选。
为了进入课题组,席萱曾拒绝一所C9高校的保研机会,转身投入考研。她认准了那位导师,相信这个实验室能带来更好的科研机会。
与席萱一样,Eva的“研究生入场券”同样来之不易。她大一选了十五门课,清晨五点起床,八点准时进教室;白天排满课程,晚上要“肝作业”、准备各种比赛,常常一坐就是深夜。有时一周连轴转,几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睁眼就在教室。这样的自律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大学生活。
同样决定退学的工科生周望是二战考研生,两次都坚持考的原专业电气工程,二战落榜后被调剂到了新能源汽车方向。
他们曾一度把“研究生”视为通向理想人生的必经之路。席萱幻想自己一路科研升阶,最后成为高校导师,家人都为她感到骄傲。周望虽然是跨专业起步,但一边自学补课一边完成任务,从未松懈。他们都在那个起点上,真诚又用力地想把命运向前推一把。
因此,退学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从第一次冒出“退学”的念头,到真的走到这一步,大多数人都挣扎了好几个月。
农学专业的庞程那会儿已经情绪崩得厉害。半个月里,她几乎每天失眠到凌晨三四点,醒来还得去实验田干活。有天凌晨四点才上床,两个小时后她又站在田地里,身体没来得及暖和,脑袋眩晕得快站不住。可当她向父母倾诉自己的崩溃时,换来的却是:“你再坚持一下。”
庞程早上在地里干活
周望第一次跟家里提退学,是在研一的十月份。他在电话那端犹豫半天,家人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毕竟考研二战成功、调剂上岸实属不易,怎么可能说退就退?
席萱则背负着更深的内疚。她频繁回家或跑到大理,借口说是散心,实则是在逃避。
她注意到,家人们对她读研这件事赋予了过度的象征意义:“我不用带礼物,也不用做出成绩,只因为我是研究生,他们就对我另眼相看。如果我退学,他们就不会以我为傲,而是以我为耻了。”
通向理想的门票,进入的却是围城
研究生阶段与本科的最大不同,在于重心从“学习”转向“研究”。不再是按部就班地上课、写作业,而是要围绕一个课题开展系统性的科研工作。
这种转换,对很多人来说并不自然。几乎所有“卡壳”的开端,都是从科研压力开始的。
周望选导师时做了很多功课。他本科是电气工程,担心跨专业吃力,就挑了一个仍和电气有交集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借助过往积累,减少起步难度。但他很快发现,这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预设。
在第一次和导师交流研究计划时,他提出了一个基于本科背景构思的选题,没想到导师当场否决,理由是“组里已经有人在做”。紧接着,导师给他指派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这对周望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试探着问,能否让高年级的同学带一带,导师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人能带。”换句话说,一切都得靠他自己摸索。
自那之后,每周一对一的组会成了他最紧张的时刻,导师像一个只等结果的“项目老板”,永远只抛出一句:“做得怎么样了?”而他没有资源、对研究主题又毫无经验,只能硬着头皮上。
Eva则是在别的地方撞了墙。她一路高考保送、名校加持,留学、创业也都尝试过,履历上满是光鲜。研究生阶段,她选择了金融方向,但并非出于兴趣,而是顺应家人“这么好的成绩不能浪费”的期待。
起初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学习投资、银行等课程,却很快感到吃力。真正走入实习岗位后,这种不适感更为明显。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对金融的理解并不扎实,对行业节奏和逻辑也很难共情。“我可能真的不适合这条路。”她开始怀疑。
但现实也没有给她留下太多喘息的空间。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的报告,金融行业的“黄金时代”正在远去。投简历的人数同比增长近46%,而校招职位却大幅缩减,岗位供需比飙升至5:1。
Eva不禁思考:即使咬牙坚持毕业,又能怎样?那些她曾憧憬的西装笔挺、言辞利落的金融人形象,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泡影。
Eva在做金融实习时在茶水间拍下的照片
在科研之外,还有更隐性的挑战:实验室,也是人际冲突与权力结构的角力场。
大四那年,庞程保研后提前进入实验室熟悉,一开始的热情很快被浇灭:没有人欢迎她,也没人介绍她是谁。导师只递给她一张排班表,上面写着待完成的“活儿”。她只能跟着一个同级同学含糊学习,剩下的任务都是靠自己摸索。
彼时,课题组正执行一个大项目,由三位博士主理。庞程被安排参与棉花纤维处理实验,按照轮班表每两天出一次工。暑假,她被默认要跟着师姐下地干杂活——浇水、施肥、自交杂交,顶着烈日,忙活到夜幕降临,毕业假期也不翼而飞。
过程中,庞程慢慢领悟了这个体系的真实法则:“没有谁来教你,没有谁来扶你,大家都只是资源分配中的可替代劳动者。”老师是发号施令的“老板”,学生则成了随便使唤的“工具人”。她苦笑着说:“我比较好说话,所以大家都把活分到我这里。”
在庞程的研究生生活中,最令她深陷困扰的,是一位外表和气、实则处处耍心眼的师兄。
这位师兄刚到实验室不久便让她帮忙做实验,名义上是“带一带新人”,实际上是把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全数转交出去。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师兄从未亲自做过一次实验,却始终在群里的排班表上挂着自己的名字。“他明明什么都不做,却装得比谁都积极。”庞程说。
一次实验中,庞程终于崩溃了。她扔下手里的工作,冲出房间,站在走廊尽头拨通妈妈电话。电话一接通,情绪已先一步溃堤:“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庞程在地里干到晚上7点拍下的照片
不久之后,又一件小事把她压得喘不过气。那段时间母亲从老家赶来看她,她提前跟一位师姐商量换班,对方答应了,还把新排班表发到了群里。她照表上了岗,却在几天后得知,自己的名字依旧出现在原来的时间段。师姐解释:“有人反映你干得太少,又补了一次。”
后来才知道,那位师兄私下说她偷懒,建议大家多安排些工作给她。庞程去找师姐,师姐让她找老师,她硬着头皮跟老师解释自己已经完成了工作,可老师根本不听,只冷冷地说:“排都排你了,你就再去一次。”语气里甚至有些不耐烦,“下次会少排。”
那一刻,她忍无可忍,声音哽咽:“我妈来了,我都还没见她一面,我真的已经做过了,而且平时活儿也最多。”导师脸一沉,说道:“我们课题组就这样,适应不了就走人。”
当退学成为一种选择
即便在痛苦而挣扎的研究生生活中,他们早已对光鲜的科研履历、鼎鼎大名的导师和看似体面的学术环境完成了某种“祛魅”,却依然无法下定决心离开。直到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出现。
对庞程来说,那根“稻草”是一个国庆节的电话。当时她刚刚申请调到新的导师组,相比之前组内的压抑感,这里让她稍微松了口气。
10月2日,她和一位高中同学回老家聚会,随手发了条朋友圈,记录下久违的家乡夜色。结果,这条看似平常的动态引来新导师的质问:“怎么一声不吭就回家了?”
庞程懵了。她觉得国庆回老家很正常,但导师却认为她“不敬业”。庞程心里说不出的委屈和不甘,那一刻她动了真念头:我要找工作,不想再上学了。
庞程离开武汉时拍下的照片
周望向辅导员表达退学意图后,导师暂时将汇报频率从每周调整为每月。起初,他以为获得了喘息空间,可汇报次数虽少了,每次电话仍旧是那句:“做完了吗?”他听着那句问话,常常觉得荒唐——在没有任何支撑、缺乏方向的前提下,又要怎么凭空交出成果?
在对退学犹豫不决的时间里,席萱常常失眠。
她觉得实验室像一个小人国,所有人都专注于用精密仪器观察微小的结构,沉浸在对细节的掌控感中。但正因为“看得太小”,这个系统常常忽略了更广阔的维度,比如人类的感受与情绪,每个人都不敢表达疲惫、不满或者反抗。一旦有人尝试表达这些不那么“理性”的内容,反而会被视作软弱、可笑。
为了逃离压抑的环境,每天傍晚六点,席萱都迫不及待地冲出实验室,在小区广场与孩子们一起玩轮滑。他们的欢声笑语是她一日中最真实的慰藉。
他们开始尝试从说服自己开始,再一步步去说服身边的人——让“退学”成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决定。
庞程和妈妈进行了一场严肃对谈。她坦承,这些年她一直在按别人的剧本生活,从未探索过自己的方向。研究生生活不仅没带来成长,反而像抽走了原本属于她的那股活力和真实感。妈妈静静听完,过了很久,她终于点头,接受庞程的选择。
席萱的妈妈陪她去大理散心。在回民宿的出租车上,席萱试探着开了口。她说,其实像司机这样的工作,也能给别人带来真实的价值,也可以开心,“你看,开滴滴也挺不错的。”
妈妈没有反驳。席萱顺势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所以,我准备退学了。”
妈妈轻轻劝了句:“还是读完再走吧。”
但席萱没有退让,这一次她坚定地说:“可这是我的人生。”
车厢内刹那静默。妈妈终于说了一句:“那你和你爸先别说,我来帮你。”那一刻,席萱知道,母亲已然站在她这边。
席萱拍下的大理美景
那天她们来到洱海边,大风拂面,气温微凉,却让母女俩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湖面泛起涟漪,远山静谧,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这是属于她们的平静时光。
“有人说你勇敢,也有人说你在逃避”
像从某种长期的压迫中挣脱出来,退学给他们带来的是难以言喻的轻松感。但很快的,这份轻松就被另一种情绪取代——茫然。
席萱把这种感觉形容为“非痛苦的失重”:就像被猛地从地面拽起,漂浮在空中。
她像个犯下“大坏事”的人,等待着未知的审判。离开实验室,意味着人生真正由她掌握,她一边默念“别怀念过去”,一边告诉自己不要恐惧。
在决定退学之后,每一次来自他人的理解与支持,都变得格外珍贵。他们曾长时间陷于否定与自我怀疑之中,因此任何正向反馈,也能成为支撑他们往前走的力量。
庞程去找研究生辅导员签退学手续时,其实做好了心理准备,以为会遭到劝阻。
但让她意外的是,对方并没有试图挽留,反而平静地说:“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那一刻,庞程热泪盈眶。
退学后庞程朋友给她写的字条
庞程投了上百份简历,最后选择进入一家电商公司做管培生。面试时,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问到她的退学经历,她选择如实作答。有的人听了之后表示不理解,问她为什么不把读研坚持下来;有人断定她会后悔;也有面试官只是点头说知道了。
周望一开始也想过是否要隐瞒,但后来他觉得真诚更重要,“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你有勇气,也有人觉得你是逃避,但最终要选的是那个能和你价值观相合的人”。
Eva她曾是那种典型的“做题家”,从河南小镇一路答题出线,考入国内顶尖高校。如今,她才渐渐意识到,人生不是一场持续的选择题考试,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退学后,起初她按照惯性继续“答题”——实习、面试、进入光鲜的金融机构和大厂,见识了职场最前线。可那些原本被视作人生“满分答案”的经历,并没带来预想中的成就感。
现在,她尝试做一名主播,对她来说,“既然退学了,就要改变得彻底一点”。
Eva工作时的个人形象
席萱退学后搬去了大理,在古城上脱口秀开放麦,每周都上台讲段子,也做起了自媒体。舞台下的观众来来去去,有时会有人在她的社交平台留言,问她怎么舍得在研三退学——“就差一点点,不拿个学位太可惜了。”
面对这些质疑,她曾试着解释,后来干脆换了一种方式来形容那场退学——
“就像一场离婚”。
如果说结婚是为了幸福,那么离婚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接受‘升学’这个决定,仿佛它天经地义,却羞于承认‘退学’也可能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式。”
在席萱看来,那些让人崩溃的实验室、沉默的导师、无法呼吸的节奏,是一种不适合她的“婚姻关系”,而她只是从一段不适合的关系中走出来。
“退学是我重新选择生活的起点,是我为自己争取的第一份自由。”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