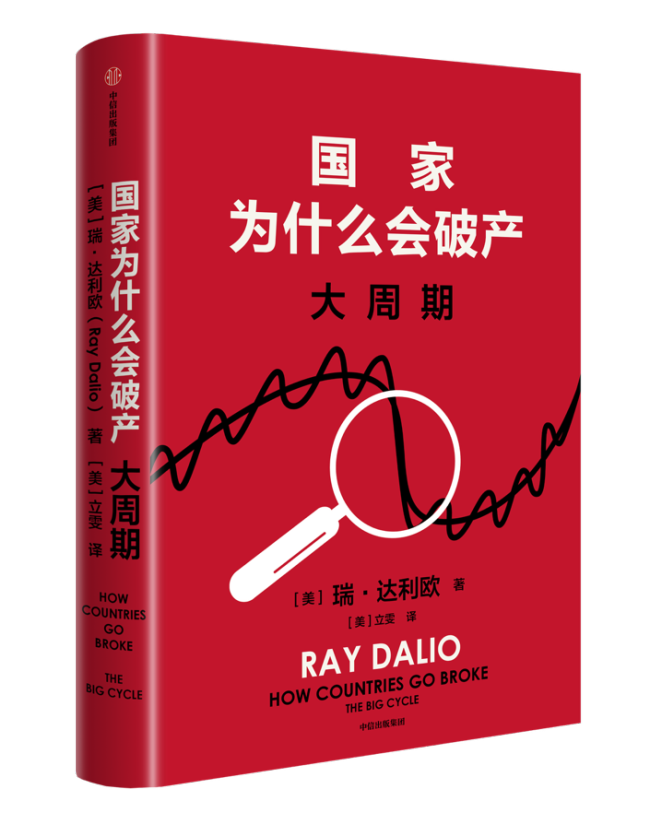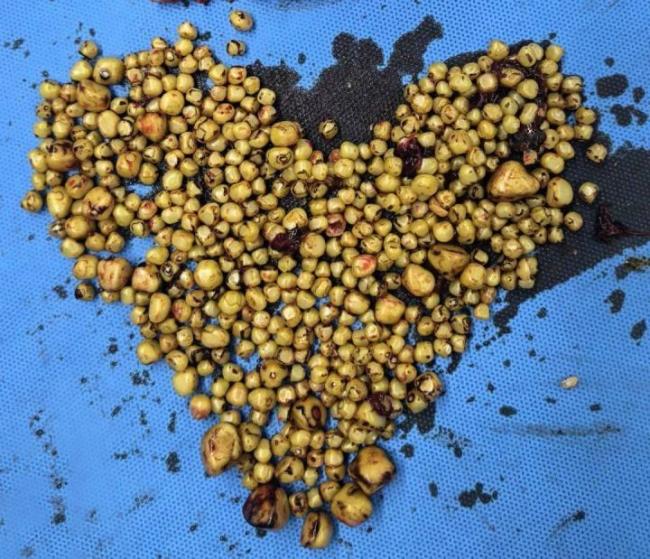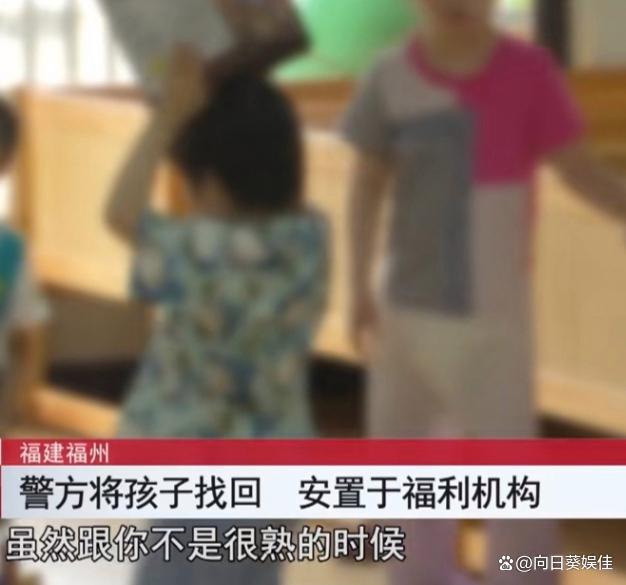《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在国家盈亏的时间表中定位我们自己 书评 债务周期下的大国博弈
《国家为什么会破产》:书评揭示债务周期下大国博弈的真相,本书通过国家盈亏的时间表,让读者了解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和后果,作者深入剖析国家破产的原因,引导我们思考在全球经济环境下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本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国家财政的重要知识,还启发我们认识到在全球经济波动中如何定位自己,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在国家盈亏的时间表中定位我们自己 书评 债务周期下的大国博弈。达利欧先生的读者对他的大历史著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并不陌生。但相比之下,《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给我的启示更多。《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探讨了荷兰、英国和美国三个全球储备货币国家的兴衰周期,而中国人对于帝国兴衰的经验已有两千年之久。然而,《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讨论的是国家债务周期,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只有100多年,具体来说是从1880年到1945年以及1978年至今。前一段是我们的过往,后一段则是我们的当下和未来。如果一个人想从国家债务角度理解中国100多年来政治秩序的大震荡与重组,这本书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达利欧在书中将经济系统分为五个核心部分:商品、货币、信贷、金融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商品和货币容易理解,例如你用现金购买一辆车,交易完成,双方两清。历史上很长时间内,这些交易不是靠主权货币完成的,而是靠天然货币如黄金和白银完成的。当你能保证硬资产交易持续进行时,就可以发行信贷。信贷允许你在短期内获得远超支出的收入,但未来需要以更高的支出偿还。比如一家造车厂拥有强大现金流,可以发行信贷在市场上借一大笔钱增加短期收入,最终通过扩大产能赢得更高收益。本质上,信贷是对未来的溢价交易。当信贷诞生后,我们可以继续交易这些信贷,如股权、债券或股票,这构成了金融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现代经济体包括这五个部分,且越是先进的经济体,信贷及以上的部分占比越大。
我们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公司,其产品是一系列公共物品,包括道路、水源、公立学校、法律共同体、警察队伍和军队等。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自文明开始,国家就学会了向民众征收实物物资和劳动力。因此,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模式是在产品和服务中维持平衡:如果税收过高而提供的产品不足,人民可能会通过内战或革命抛弃它。随着国家获得硬通货的能力提高,它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在短期内增加收入。这就是主权国家信用货币的诞生,例如1694年英国政府成立英格兰银行发行国债,提供的票据就是纸币英镑。
国家发现了一种新的、利润更高的产品:纸币。国家面临一种诱惑:既可以通过发行纸币盈利,又能垄断国境内的暴力使用权。许多国家没有抵制住这种诱惑,如中华民国发行金圆券。但想抵制诱惑的国家可以采取三种办法:有一个限制暴力使用权的民意机构(议会)、保证央行独立性、承诺主权货币与硬通货的兑换关系(金本位)。当一个国家拥有这三大支柱时,我们就把它称为现代财政国家。
现代财政国家的权力看起来缩小了,但实际上能力扩大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凭借政府信用战胜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金本位崩塌,主要工业国货币挂钩美元,美元挂钩黄金。但1971年,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此后,国家通过发行货币赚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央行发行货币不再需要承诺兑换硬通货,而是通过加息或降息调节货币供给,或通过外汇交易平衡汇率。国家面临新的诱惑:既然货币发行摆脱了硬通货限制,为什么不无底线地超发货币?约束力量来自货币的产生和运行机制。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主要的债务活动来自市场中的各个行为者。1971年前的央行把自己看作债务人,而1971年后则把自己看作做市商。债务人关注如何偿还硬通货,做市商关注货币资产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交易状况。央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短期债务下行周期通过逆周期操作鼓励借贷消费的诱惑总是更大。最终,债务及偿债支出会像恶性肿瘤一样持续蚕食实际购买力,挤压正常消费空间,这就是长期债务周期的根本来源。
达利欧为国家债务周期画出了大致的时间表:短期债务周期一般持续6年,很多个短期债务周期最终积累为约80年的长期债务周期。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经完整经历了12个短期债务周期,目前第13个周期已过去三分之二。但就长期债务周期来说,它正处在中后部分,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这一轮长期债务周期的各个阶段如下:
1. 1945-1971年,挂钩硬通货的货币体系。 2. 1971-2008年,由利率驱动的法定货币体系。 3. 2008-2020年,债务货币化的法定货币体系。 4. 实施协调型大规模财政赤字与债务货币化政策的法定货币体系。 5. 大规模去杠杆化。 6. 回归硬通货。
债务周期只是决定大国兴衰命运的一个变量,还有内战、国际战争、自然力量和科技力量。美国当前处于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过渡期,真正让人难受的“去杠杆化”时间还没有开始。如果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可能引发大规模地缘政治危机。
不过,美国的危机不代表美国无法从中恢复,也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会从中获利。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央行创造货币和信贷的周期与美国基本同步,甚至更早。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购入债务。2016年中国央行比美国更早开启去杠杆化周期。如果中国实现“和谐的去杠杆化”,并比美国更早结束去杠杆化周期,那么中国可能会有远超预期的表现。
很多人用地缘政治对抗视角看待中美博弈,但从债务周期角度看,中美博弈很大程度上是个时间差问题:哪一方更早实现“和谐的去杠杆化”,避免进入死亡螺旋,同时缓和其他四大变量中的内战和国际战争,并实现科技突破,哪一方就可能在大博弈中占据阶段性优势。大国不死,一时的输赢从长期来看只不过是优势阶段和劣势阶段的时间错位而已。
达利欧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揭示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定会依赖发币赚钱;其行为模式符合周期规律。这个周期规律像航行中的指南针,帮助我们在洪流中找到时间表并进行自我定位。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在价格和价值的错配中获得利益的活动,一个投资标的的价值由其本身决定,但其价格经常由货币周期决定。在时间表的上行阶段,抓住货币扩张的大势就能成功;但在时间表的下行阶段,理解货币周期的定位也可能预判央行和各个行为体的行动,发现被情绪错杀的投资对象,从而实现盈利。
此外,我们还可以展开对未来想象:大债务周期结束后,主权货币会挂钩什么硬通货?是黄金、加密货币、工业品制造能力,还是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算力?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逻辑起点都可以从达利欧这本书开始。无论是帮助我们理解宏大叙事,还是指引我们过好日常生活,这本《国家为什么会破产》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