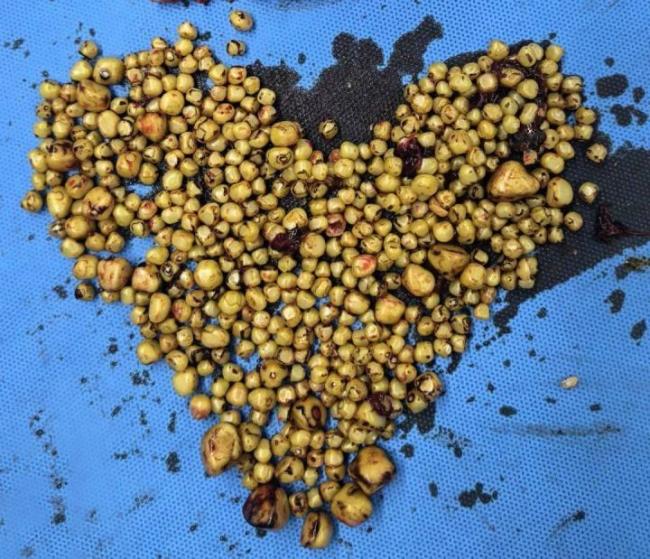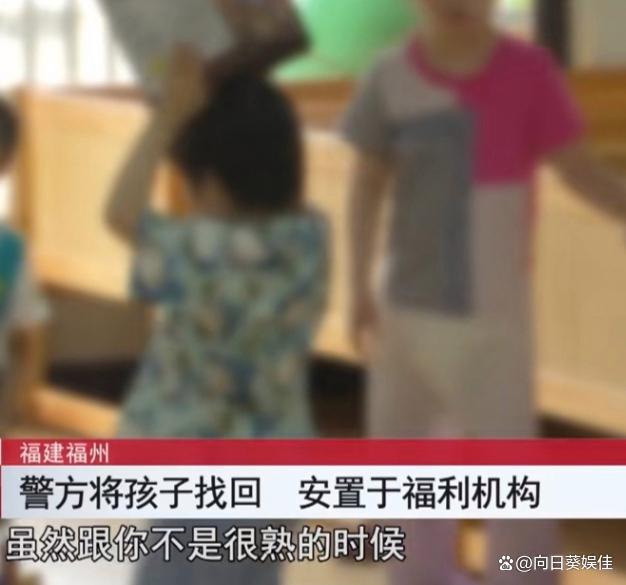北约“5%团结”背后是被扭曲的跨大西洋关系 欧美裂痕加深
北约内部出现的“5%团结”现象背后反映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扭曲,欧美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这一现象揭示了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不和谐,以及欧美之间在多个领域的分歧和矛盾,这种裂痕的加深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贸易摩擦到防务费用分摊,从俄乌冲突到对华政策,美欧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转型挑战。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不久,欧美关系很快就迎来一次重击。在今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讲话中直斥欧洲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其内部在“欧洲与美国共享的最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万斯还指责欧洲国家领导人“对反对者进行审查”“害怕自己的选民”,并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大规模移民问题。万斯的讲话如同一颗深水炸弹,使得此后两天的慕安会议程完全被颠覆和重塑,人们关注的重心转向跨大西洋关系危机。
此后,特朗普政府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挥起关税大棒、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成本等一系列动作无不使欧美关系大受冲击。7月3日小组讨论的互动环节中,有记者向与会嘉宾提问,对于跨大西洋关系来说,特朗普只是四年的短期挫折,还是会为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美欧关系设定方向?美国欧亚集团主席克利夫·库普坎表示,他并不认为美欧关系的大趋势会发生变化。他指出特朗普曾经就差点失去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预测其会在明年中期选举中在众议院遭遇失利。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并不相信特朗普的对欧政策逻辑,随着鲁比奥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可能会改变很多东西。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拉雷斯则同样对美欧关系的发展前景作出乐观回应,他表示,很多人通过特朗普认识了美国,而特朗普不能够代表美国最好的那一部分。不论美欧在贸易上有再多争端,人文交流依旧可以对双方关系发挥很好的作用。
有人认为,欧洲对安全的关注似乎已经超过了经济议题,因此在多方面对美国作出过多妥协和让步,这种过分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很大程度上给欧洲的自主和发展拖后腿。西班牙驻华大使贝坦索斯表示她也听到了“欧洲成为美国附庸”的声音,但她认为这是一些误解或者错误的认知,欧洲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有自己的要求,同样也有对中国的真实期待。她还指出,欧洲要处理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战略眼光来看待自身问题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投资等,都有必要进行沟通交流以平衡双方关系。
北约峰会刚刚落幕,尽管成员国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支出提高至本国GDP的5%,但除了西班牙之外,斯洛伐克和比利时也暗示这一承诺将无法兑现。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尼法斯指出,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原则虽然是西方国家战后赖以依存的安全基石,但这一保护并非没有条件。在特朗普对北约产生质疑之后,欧洲国家愈发意识到这种依赖的代价。他警告,北约要求成员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5%,不仅不现实,也将削弱联盟的可持续性。欧洲国家必须认清美国支持的不可持续性,“欧洲战略自主”并不等于脱离联盟,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贝坦索斯则表示,跨大西洋关系已不再是冷战意义上的“北约关系”,而是一组亟需重新定义的多层次联系。在全球化带来结构性依赖与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下,欧洲应警惕过度依赖安全联盟所带来的局限,特别是在美国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今天。当防务预算成为各国争论焦点时,更重要的是讨论“如何用预算实现真正的安全”,而非盲目堆砌数字。库普坎作为一位曾担任政府官员的美国政治分析家,则对北约的未来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虽然北约内部确有信任危机,但并未如舆论渲染得那样严重。特朗普虽多次批评北约,但短期内无力推动美国退出该组织,也不太可能撤军。他判断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主动挑战北约第五条的“集体自卫”条款,欧洲真正的危机仍集中在乌克兰战场。但他也指出美欧关系确实存在较大的问题,美国对欧盟的战略定位早已从“伙伴”转为“竞争者”,贸易摩擦、关税威胁不断反复。结构性不稳定成为美欧关系的最大挑战,而对中国的政策将成为另一变量,欧洲或在美欧关系承压下适度寻求与中方改善关系。
拉雷斯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欧洲目前在对美关系中被迫“依赖”,甚至“讨好”特朗普,哪怕以一种他所称的“卑劣方式”换取对话机会。这种不对等博弈损害了欧洲的尊严与自信,也使得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扭曲。拉雷斯明确指出,特朗普正以“放弃乌克兰”的方式重塑其外交逻辑,未来三年内若无重大转变,乌克兰可能在军事援助缺席下走向失败。他同时警告,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盟存有敌意,支持民粹主义者在欧洲扩张影响,这种趋势一旦继续,将对欧洲制度基础构成威胁。尽管如此,拉雷斯也强调,美欧关系恶化并不意味着欧洲就会自动向中国靠拢。欧中关系仍属结构性竞争,“去风险”而非“脱钩”仍是主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