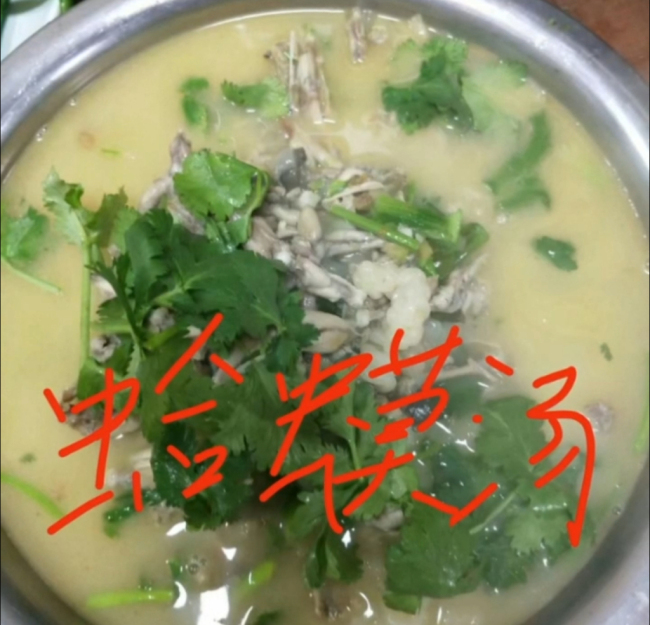大厂高管裸辞 从年薪百万到月入三千
大厂高管裸辞,从年薪百万骤然降至月入三千,这位高管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辞去高薪职位,选择重新开始,他的决定反映了现代职场中人们对生活、工作的重新思考,敢于面对挑战,追求自我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平衡,此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高薪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大厂高管裸辞从年薪百万到月入三千。
李岩是一家知名大厂游戏业务的部门负责人,曾管理大型的研发团队。去年年初,他放弃了几百万的年薪和股票,从原本蒸蒸日上的岗位和业务上离开了。裸辞。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但在他的视角里,做高管也有高管的烦恼,表面光鲜的背后,反而更需要去回答“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离开之后,他重拾过去画画的爱好,并通过画画认识了不同于大厂的人和生活状态。但他也发现,书画圈是个名利圈,有很多人情世故、争夺纠纷。相比之下,大厂是个功利圈,一切以效率说话,是另一种残酷。
我们的访谈在去年9月进行,因种种原因,文章到现在才发出。最近,再联系李岩,他有了新的动向,即将加入一个创业项目,开始新的折腾,新的跋涉。以下是李岩的讲述。
裸辞
我是去年3月份提出来离职,4月份离开公司。提离职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大学毕业就进入大厂,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干就是19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更何况是裸辞,所以也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告别。
临走前我给老板写了封长信,现在想想挺傻的。字里行间全是“建议优化人才梯队”“基层员工缺乏价值感”之类的废话,活像个交不出毕业论文的大学生。这是很幼稚的行为。
问题大家都知道,只是所处的的角度不一样,解决方案也不一样,而我也是很局限的。老板的办公桌上永远堆着更重要的文件,而我这种“谏言”就像在海啸里扔救生圈,除了感动自己,啥用没有。
我特别跟老板强调两点,我不是因为遇到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要走,也不是要谈什么条件。而是这几年确实蛮累的,到40岁这个年纪,想休息一下。
离职的时候,很容易回顾自己的整个职场生涯。某种程度上,我算得上是这个职位打工牛马的天花板。
我在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但我从小学开始特别喜欢画画,高中读的是美术高中,大学想考中国画专业,理想是做个画家。没想到,最后阴差阳错地学了广告专业。2005年,我大学毕业找工作。那年互联网还不普及,不像现在,哪家大厂什么管理风格,连伙食、福利待遇,年轻人都一清二楚,找个工作,能投几十家公司。当时我只投了一家公司,通过了,月薪三千。这已经是我们专业的天花板了,远超自己预期,也就没有再去看其他机会了。
入职一直到离职,整整19年,我再也没有换过工作。在这个行业里,能熬到42岁还没被35岁危机拍死的,本身就自带某种幸存者光环。那些曾经一起入行的兄弟,有的已经转行去卖保险了。
那时候国内的游戏行业刚刚起步,大家都是处于扫盲学习的阶段。最开始公司就像一间学校,每天都能学到很多新技能,工作3个月,比大学4年学的东西都多。大家互相称呼老师和同学,很包容,甚至有点草台班子,招进来的很多人学历水平并不高,公司流程也不是那么正规,很多年里我都感受不到有人力资源部门的存在。你想想这是多离谱,这么大一个厂。
管理也很松散,不像现在的大厂,有十几个层级,一层一层往上汇报,我们这很扁平,互相之间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各部门的自主权也很大。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公司对人才的规划也比较长远,会考虑一个人在公司至少3-5年里是什么水平,什么定位,将来要让他参与哪些项目,承担哪些责任。
不像现在有些厂,看似招了很多高端人才,实际上都是缺哪补哪,缺个总监,就去市场上招一个总监,把人和位置都钉死,公司就缺这个,不允许你去干别的。
就是这样宽容的环境里的,诞生了很多成功的产品。游戏本身是一个创意行业,非常需要土壤和氛围,搞创意的人需要被尊重,被信任,需要激发潜能。这种潜能不是通过“钞能力”就一定能激发出来。
很多优秀的产品,都是草台班子做出来的。创作者们不一定是多精英,甚至可能是校招进来没几年的新人。只是草台班子有钱了以后却很难再次成功,这是这个行业的魔咒,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也赶上了端游转手游的美好时代。前后参与过的产品少说也有百来款了,总流水千亿应该是有的。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但就是发现,时代的浪潮推着我到了浪尖的地方。
随着公司越来越大,团队规模也越来越大,自己的能力确实也难以适应新的发展,当我力不从心的时候,我选择了做个逃兵。
离职也许是我能为公司做的最后的贡献了。
高管的烦恼
当一个行业处于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人人都有机会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被掩盖和忽视,游戏行业也不例外。但一旦进入存量市场竞争,就会内卷。
《原神》爆火那年,我们会议室里的气氛一度变得很紧张。领导每周必问的问题从“今天下午茶吃什么”变成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出原神”,于是整个部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思运动”。
反思问题是个好事情,缺乏反思,很难进步。但职场上的反思,往往不是反思自己,反思的都是别人的问题。通俗一点讲,就是“甩锅”,尽量把锅甩到别人头上。可以说是当代职场人必备的技能了。
氛围逐渐变了。以前那种充满学术氛围的松弛感消失,大家都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体现自己的业绩,表现一把。听起来似乎是个好事情,但坏就坏在,有些人动了歪心思,会不顾实际情况地包装自己的数据和业绩,干一些指鹿为马的事情。
大厂都在降本增效大背景下,明明100万才能完成的项目,硬有人跳出来说10万就能干,谁都知道这跟说“我能徒手捏出光刻机”一样离谱,但在降本增效的大旗底下,没人敢做第一个拆穿皇帝新衣的小孩。
合不合理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对方卷死,自己才能保住这份工作。这有点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低价竞争,明明已经不挣钱了,但是没办法,把对手卷死才能上牌桌。向下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昧着良心做低质量的东西。
还有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PPT秀。明明是改了三个按钮颜色的小优化,非要写成“基于用户行为大数据的交互逻辑重构”,配上3D建模的流程图,最后用20页篇幅论证“为什么红色按钮比蓝色按钮转化率高0.3个百分点”。
屁大点的工作,写100页PPT去汇报,工作3分钟,写PPT俩小时,为了在职场中活下去,天天揣摩老大的想法——很典型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其实也不是啥坏人,能进大厂,业务能力都差不到哪里去,但就是为了生存,动作变形了。换个环境,他们仍是优秀员工,业务骨干。
我有没有干过这种事?肯定也干过,但确实有点不齿。
总是在网上看到大家吐槽大厂的领导、高管、老板,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看基层员工的吐槽,好像跟老板看我的视角一样,其实员工是对的,老板也是对的,只是站的位置不一样,大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大家各有各的压力。基层员工要解决的是自己的成长问题,任务有没有完成,能力有没有提升,很实际的一些事情。高管要解决的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比如要达成一个结果,但是自己能力有限,比如你只是负责其中一块,其他环节不受你控制,很多问题需要去说服别人,很难推动,很多时候就沉浸在这种痛苦之中。
这不是升职就能解决的问题,打个比方,做科长的时候,你会想,混成处长,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混成处长,问题还在;再往上走,都成市长了,你发现,还是解决不了。
高管没什么值得崇拜的,能做高管,肯定是有亮点,可能确实是业务能力比较强,可能很会向上管理,有些人情商比较高,或者特别努力,但是不要把他们神化。
高管想要引导基层的员工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奖励、考核机制,团队建设的方式方法,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很多部门又很难考核,比如技术部门,你怎么给他们定那种又大又空的目标。高管自己也担心自己。
像现在的大厂合并又分拆,分拆又合并,一直在改组织架构管理模式,但实际上,可能就创始人层面那几个人关心公司发展,再往下一个层级,大家都考虑自己的盘子——你问我要不要拆,我首先考虑拆了之后我还能干啥,对吧?
所以很多公司越折腾,越很难改,就跟癌症晚期一样,越化疗越严重。
我管理的是一个大型中台部门。了解大厂中台的都知道,这是一个让业务又爱又恨的部门,用你的时候你是小甜甜,甩锅给你的时候你就是牛夫人了。就像抽水马桶,只有坏了的时候才想起它的重要。尤其是在大家都有压力的时候,中台就需要不断去证明自己有价值,这时候就会有人冒出来表示可以用AI提效50%之类的事情,这有些荒诞。
大家都过得挺累的。
为什么大厂上班的人容易得抑郁症,按理说,能进大厂的人,学历、智商、情商都不低,收入也不低,除了工作累一点,他们已经超越绝大多数牛马了。我想这种郁闷并不是来自工作强度,而是来自缺乏归属的虚无感。
缺乏成就感引导的工作,会让人失去动力,导致很多人是带着面具假装努力,表演式工作,表演久了,要不就是自己也入戏了,要不就是抑郁了。面具戴久了,也是很累的。
做游戏开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有些人工作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成功产品,屡战屡败。经常都是忙活五六年的项目,说砍就砍了,仿佛从未存在过,让人很丧气。最近也在反思,做什么样的工作更能让人获得成就感?比如从小喜欢画画,产出了很多作品,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或者做个厨师,做了很美味的饭菜,别人吃完都很满足,这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再或者种点菜,到季节能有所收获,都是很不错的。否则人很容易陷入对抗虚无的痛苦中。
作为管理者,这些问题不应该要去解决吗?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这种系统性问题,我确实有些无力感。只能说自己能力有限,选择了逃避吧。
从功利圈到名利圈
大厂给了我很多。比如金钱回报,都是完全超预期的。我常常有一种不配得感,我的能力没有到这个层次,确实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行业和好的公司,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
现在回过头来想,并不后悔当初辞职的决定。人生永远都是在得与失之间做抉择,不能什么都想要。我是一个比较遵从自己内心呼唤的人。和很多INFP性格的人一样,在做一些重大人生抉择的时候,会表现出不理性的一面。有一说一,INFP的人真的不适合在大厂做领导。
离职后忙活了很多事情,也把画画这档子事重新拾起了,新认识了很多朋友。
画圈的朋友和大厂的朋友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群体。通过画画认识的人,来自各行各业,社会身份不一样,有学校老师,政府的公务员,打工人,退休的人……大家都蛮单纯的,有很多生活层面的体验和共鸣,不是满脑子升职加薪,买房买车。在大厂做牛马的时候,更关注效率和结果。
不过,也不能把画画想得那么纯粹、美好。
会有一种参差感。画画挣钱的效率真的远低于在大厂上班,卖一年画的画,可能还不如在大厂拿一次年终奖。之前我在大厂的时候,约一个画手,报个几千一万的价格,人家都看不上,随便约个画师都是3万、5万的。现在我自己辛辛苦苦画画、卖画,其实也就几百块钱、千把块钱。
回头看大厂,其实像个明码标价的菜市场。你有多少能力,就能换多少薪水,虽然竞争残酷,但至少规则透明。不像艺术圈,讲究“圈子”“人脉”“师承”,有时候一幅画能不能卖上价,跟画得好不好关系不大,全看你会不会混圈子。有个画友跟我说过一句名言:“在大厂,你是被KPI绑架;在画圈,你是被人情绑架——反正都是绑架,看你选哪种绳子。”
画展上互相递名片,上面印着各种“副主席”“秘书长”的头衔,比我在大厂见过的总监还多,突然觉得挺讽刺:原来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职称内卷。
就像娱乐圈一样,画画的人想要出名、赚钱,需要包装,需要资本的吹捧,要搞好各方关系,签画廊,各方面都做到位之后,才是本身的专业问题。很多书画圈子里的人,在小地方混得很好,还能做个美协主席之类的,但他们的作品放到互联网上一看,非常普通。
站在名利圈重新回看大厂,就感觉大厂其实是一个功利圈。
相对来讲,大厂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而是凭实力说话。但是它特别残酷,丛林社会,能力行的和能力不行的,差别很大。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比如向上管理,它也是在一个看似公平的框架内诞生的。
大厂是用绩效和丛林法则在统治人。同一个赛道的产品,可能同时有好几款在做,只有一个能上线,不上线的那些就白干;就算全上线了,投入的研发成本和营销资源又是千差万别,最后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这种情况下,大厂人就比较功利,不谈情感,只解决问题,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可能会痛苦。但你说,职场上口碑不好、很离谱的人,生活里有没有可能对家人朋友还是挺好的?非常有可能,大厂让人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
作为管理者,面对这个功利圈,只做一个老好人肯定不行。人本身肯定是平等的,但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结果上,分三六九等,要不然就对另外一些人不公平。
在大厂,我裁过很多人。我能理解大厂决策的原因,追求高效,降本,很合理。但是站在被裁的人、其他人的位置上,会觉得它是一种整体性的荒谬,是这个时代的荒谬。
40岁才懂的事
2021年,父亲突然离世,像一场毫无预兆的谢幕。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生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长。我们这代人,从农村的泥巴路一路走到城市的玻璃幕墙下,经历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精神上的撕裂。父辈的生活像一部黑白纪录片,而我们却活在4K高清的魔幻现实里。
作为农村的孩子,父辈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差别实在太大了。有些话我也说不出来,比如我爸在地里割玉米,我怎么跟他说,工作汇报上有点问题?很割裂。我曾以为孝顺就是打钱、买衣服、接他来城里住。可后来发现,他花不掉那些钱,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也像困兽一样不自在。
直到他离开,我才明白,有些情感注定无法对等偿还。父母给我们的爱像一笔无息贷款,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把这笔债转给下一代——并且别指望他们还。
内卷的这几年,我确实心态也不太好,按部就班地跑着。KPI、晋升、年终奖,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人都麻了。我反复地再想,40岁了,我的人生追求到底是什么?我如果继续在大厂做下去,我当然可以做得很好,可以有更多的钱,但这些钱留着干啥?买更大的房子?再买更好的车?好像意思也不是特别大。
想到我父亲,人生难道就是那样,辛辛苦苦地过,社会设定了一个时钟,你就像机器一样,按部就班地去做,最后到60岁退休。到那时候,可能心理上比较平静,但生理上肯定是衰老了,很多事情没办法再体验。你说会不会有后悔?有些人不会,但我觉得我会后悔,因为我是经常后悔的一个人。
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些明星,成功了、很有钱之后,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过得好吗?他离婚了吗?他是不是去世了?有时候看到一些文章,再去翻一翻资料,会发现,有些人可能过得比以前更好,有些还活跃在一线,但也有些人可能跌落了,甚至提前离开,或者得了抑郁症。走到特别红的阶段好像不难,但要走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
我觉得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不去折腾,光是游山玩水,那挺痛苦的。
离职前那段时间,我有点抑郁。觉得不管了,先休息一下。可能哪一天我突然就走了呢?辞职后开始报复性学习画画,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师,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成功、很有名了,却活得像个隐士。他把对于艺术的追求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沉浸在自己的爱好当中,也用爱好来排解寂寞。
六月份的大热天他带着我们在户外写生,从早改画到晚,汗流浃背却乐在其中。我问他图什么,他反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古人爱画兰竹吗?因为兰草没人浇也活着,竹子砍了节还在长。”
我现在的生活挺“不务正业”的。每天早上起来画画,偶尔见一见狐朋狗友,吹吹牛。朋友说我这是中年危机,我倒觉得是终于活明白了。毕竟人生就像水墨画,重要的不是涂满整张纸,而是留白处的那份从容。这段时间像是一场漫长的“去工业化”改造——没有目标,没有节奏,全凭感觉。
偶尔路过以前的办公楼,看着灯火通明里的加班族,还是会恍惚。但现在的我,再也不会为了一个PPT加班到深夜,也不会为了一个KPI焦虑到失眠。人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可以不断修改的草稿纸。这年头,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追求没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奢侈